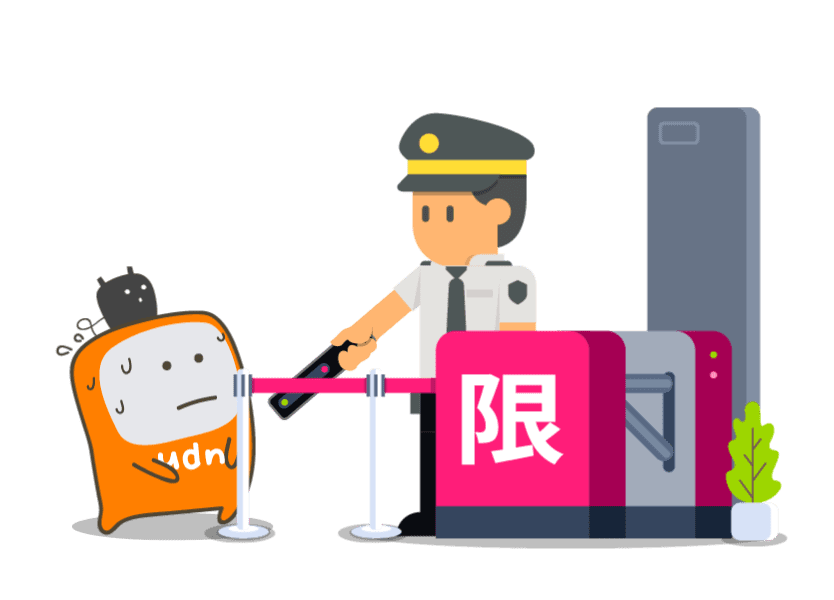LIVING IN A QUIET PLACE|活在靜音的世界,安靜成為求生之路
 活在靜音的世界,安靜成為求生之路。(圖/擷取自pexels、canva製作)
活在靜音的世界,安靜成為求生之路。(圖/擷取自pexels、canva製作)
《噤界》的電影恐懼感,漸漸的融入現實生活
在電影《噤界》(A Quiet Place)裡,人類為了活下去,必須壓抑每一個聲音。一聲咳嗽、一個腳步、一句話,都可能引來死亡。那是虛構的恐懼,如今卻越來越像現實。在高鐵車廂、餐廳、捷運裡、飛機上,父母開始提前學習道歉,學習為孩子的聲音道歉。而孩子學會壓低聲音,笑聲被掐斷、話語被吞回,安靜成了被社會大眾接納的代價。
「我不是討厭小孩,只是家長不會教。」這句留言在網路上屢見不鮮。它看似理性,卻像一把無聲的刀,切開了溫度與共感,也切斷了對孩子與父母的理解。於是,公共空間成了一場沒有怪物卻充滿審判的片場,誰太真實、誰太吵鬧、誰家的孩子不夠乖,都可能被拍下、被上傳、被貼上標籤,然後開始公審,卻忘記詢問「他/她發生什麼事?需要幫助嗎?」。
那是一種無聲的威嚇,讓人們開始相信:安靜比真實更安全。
 笑聲被掐斷、話語被吞回,安靜成了被接納的代價。(圖/擷取自pexels)
笑聲被掐斷、話語被吞回,安靜成了被接納的代價。(圖/擷取自pexels)
當被聽見,成為風險
在這個社會裡,「被聽見」逐漸成為一種風險。聲音不再是交流的橋樑,而成為被放大的錯誤。父母不是不懂規矩,而是害怕自己「沒有被理解的空間、時間」。他們提前安撫、主動道歉,因為害怕被拍下、被評論。當聲音變成威脅,情緒成就了無數的「錯誤」。久而久之,我們養成一整個懂得「自我靜音的世代」,大家開始學會「壓低音量,或是不說話」。
孩子則從大人的表情與肢體中學會另一種語言——不是「請安靜」,而是「不要被聽見」。
 孩子從大人的表情與肢體中學會另一種語言——「不要被聽見」。 (圖/擷取自pexels)
孩子從大人的表情與肢體中學會另一種語言——「不要被聽見」。 (圖/擷取自pexels)
誰有資格要求他人安靜?誰又應該被要求安靜?
「安靜」逐漸成為一種權力語言。大人可以講電話、開會、開懷聊天,但孩子只要多一句話,就會被視為打擾,遭來數落或是白眼對待。我們不敢制止講電話的大人,也不敢提醒在車廂裡高談闊論的人,因為【無數的社會經驗】告訴我們,那可能引起衝突、甚至危險。
但孩子和家長不同——他們柔軟、無害,容易被指責。多數父母不是不知道不公,而是為了讓孩子安全、不被波及,只能選擇沉默、低頭、假裝沒聽見。這種「忍讓」不是溫和,而是一種防衛。而社會因此形成一個潛規則:柿子挑軟的吃。越是沒有威脅、越不會爭辯的人,越容易成為「維持秩序」的出口。
我們口口聲聲說要維持秩序,其實只是想在不冒風險的情況下,找到一個可以安全指責的人。被挑中的,往往是孩子和他們的父母。
當文明變成一種選擇性指控,安靜也就不再是禮貌,而是一種權力。
 誰有資格要求安靜?誰又應該被要求安靜? (圖/擷取自pexels)
誰有資格要求安靜?誰又應該被要求安靜? (圖/擷取自pexels)
不喜歡用『乖』定義孩子;但「乖孩子」的定義,越來越狹隘
我們誇獎安靜的孩子、稱讚懂事的沉默,卻忽略他們的情緒正在被消音。過去,「乖」代表懂得禮貌、懂得分享、願意照顧他人;如今的「乖」,往往只剩下一個要求——不製造所謂的「噪音」。
孩子不能太興奮、不能太好奇、不能太有表情。一旦超出他人預期的分貝,就會被貼上「沒教養」的標籤。社會在追求秩序的同時,也在偷偷縮小「乖」的範圍。那些「會自己玩、不吵不鬧」的孩子被誇讚懂事,但他們也因此學會壓抑。懂得觀察大人的臉色、收起問題與情緒,因為太真實反而會被視為失控。這樣的「安靜」看似成熟,其實是早熟的防衛。
當「乖」被誤解成「不要有聲音」,社會便開始培養一整個不敢表達、也不再相信自己值得被傾聽的世代。大人們在「可被接受的安靜」中尋找安全感,那不是教養的進步,而是情緒的消音。文明若建立在壓抑之上,終將變得空洞而冷漠。
 如今的「乖」,往往只剩下一個要求——不製造所謂的「噪音」。 (圖/擷取自pexels)
如今的「乖」,往往只剩下一個要求——不製造所謂的「噪音」。 (圖/擷取自pexels)
當安靜成為禮貌與教養的代名詞,我們追求的,是秩序,還是理解?
有人說:「公共場合應保持安靜,這是基本教養。」這句話沒錯,但「教養」不該只剩靜音。真正的教養,是在不舒服的時候,仍然願意理解別人為什麼會這樣。聽見孩子哭鬧、大聲喧嘩、尖叫,我們會看到慌亂的父母、道歉的眼神,卻不願意再伸手協助,只想遠離。於是父母學會道歉,孩子學會收聲,旁人學會忽略。每個人都在表現得「有教養」,卻沒有人真的在練習理解。文明,不該靠壓抑維持,而該靠理解支撐。安靜不應是懲罰,而是一種選擇。
有些聲音甚至還沒開始,就被判定為「不應該出現」。那些還不會說話、聽不懂人話的嬰兒,在公共場合哭了幾聲,就開始有人低語:「幹嘛出門?」彷彿出門這件事,也需要先學會聽懂人話、懂得壓低聲音,才能被社會允許出現。但如果連一個還在學習表達、嘗試適應世界的生命,都必須被要求噤聲、被貼上打擾的標籤,那麼我們追求的「安靜」,究竟還是文明的象徵,還只是恐懼的延伸?
我們往往在追求秩序的同時,不自覺把「自己的舒適」當作普世標準。當「我所追求的安靜」成為唯一被接受的樣貌,我們以為那是禮貌,其實只是逃避差異。或許問題從來不在於孩子的聲音,而在於我們對「安靜」的理解。當安靜成了舒適的代名詞,也可能意味著我們正在失去傾聽他人的能力。而真正成熟的社會,不在於誰能保持沉默,而在於——我們是否仍願意傾聽那些被壓低的聲音。
文明不是靜音,而是共存。真正的安靜,從來不靠壓抑,而靠理解。